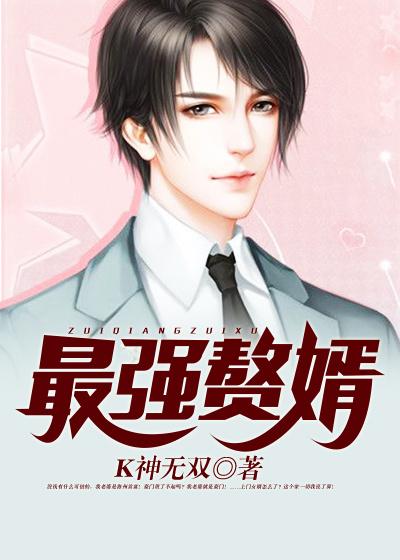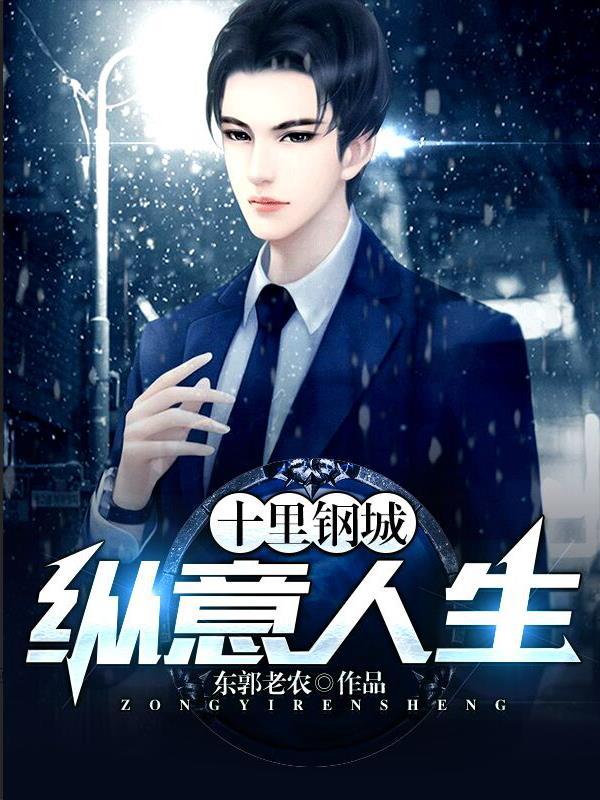腐书网>佛学研究十八篇pdf > 佛典之翻译(第2页)
佛典之翻译(第2页)
《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一卷明释寂晓撰,存佚待考。见《阅藏知津》。
寂晓,字蕴空,其书未见。唯智旭《阅藏知津》总目中列有应收入藏之书四十五种,此其最末一种也。据《知津》凡例,知其书,“但分五时,不分三藏”。又“从古判法,分菩萨、声闻两藏,就两藏中各具经、律、论三”。又“于重单译中,先取单本总列于前,重本别列于后。以先译为主,不分译之巧拙”。此智旭议其失当处也。要之此价值,当不在焦竑《经籍志》之下矣。
《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明翻沙门智旭撰,今存。旭即世所称蕅大师也,稍治佛学者,当无不知其为人。此书见日本《卍续藏经》,称四十卷。
近金陵刻经处重印本,则四十四卷。而卷首有夏之鼎序,谓四十八卷,未知有阙佚否。全书分数如下:
此书盖继王古、寂晓而作,其自序云:“王古居士创作《法宝标目》,明有蕴空沙门嗣作《汇目义门》,并可称良工苦心。然《标目》仅顺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尽美。义门创依五时教味,粗陈梗概,亦未尽善。”又自述著此书,“历年二十禩,始获成稿。……但借此稍辨方位,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其书纯为提要体,但仅列诸经品题及品中事理大概,不加论断。盖恐人“依他作解,障自悟门”。又诸经或已通行或卷帙不多者,所录皆略。唯卷帙多而人罕阅者,则详录之。凡此义例,皆极精审。唯各经论传述源流一概未及,是其短处。后有作者,因其成规,加以考证,且于通行诸经一律加详,则亦斯界不朽之业也。
二
佛典翻译,可略分为三期。自东汉至西晋,则第一期也。僧徒记述译事,每推本于摄摩腾、竺法兰,谓今所传《四十二章经》实中国最古之佛典。据其所说,则腾等于汉明帝永平十年,随汉使至洛阳,腾在白马寺中译此经,译成,藏诸兰台石室,而兰亦译有《佛本行经》等五部。果尔,则西历纪元六十七年,佛经已输入中国。虽然,吾殊不敢置信。《四十二章经》纯是魏晋以后文体,稍治中国文学史者,一望即能辨别,其体裁摹仿《老子》,其内容思想,亦与两晋谈玄之流相接近,殆为晋人伪托无疑。《安录》不载此书,则作伪者或在安后,或安知其伪而摈之也。兰之《本行经》等,亦不见《安录》,盖同为伪本[3]。是故汉明遣使,是否有其事,腾、兰二公,是否有其人,不妨付诸阙疑,而此经则绝不当信。以吾所推断,则我国译经事业,实始于汉桓、灵间(西第二世纪中叶),略与马融、郑玄时代相当,上距永平,八十年矣。
最初译经大师,则安清(安世高)与支谶(支娄迦谶)也。清,安息人。谶,月支人。并以后汉桓、灵间至洛阳。据《传》(慧皎《高僧传》也,下同),清本安息太子,出家遍历诸国,汉桓帝初到中夏,非久即通华言。以建和二年至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传》称其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道安谓:“先后传译,多有谬滥,唯清所出,为群译首。”谶,以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般舟三昧》、《首楞严》等三经,则孟谛、张莲为之笔受。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数部,译人失名,道安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传》称其译文“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凡清所译,《祐录》(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之省称,下同)著录三十四部,《房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之省称,下同)著录百七十六部。凡谶所译,《祐录》著录十四部,《房录》著录二十一部[4]。所译率皆从大经中割出小品。例如清译之《四谛经》,即《中阿含》之《分别圣谛品》也。谶译之《般若道行经》,即《大般若》第四分内之三十品也。汉末三国时所译经,大抵类此。故每部少或一卷,多则二三卷。若《般若道行》之十卷,在当时最为巨帙矣。尤有一事极可注目者,则清公所译,多属小乘,出《四阿含》中者居多,所言皆偏重习禅方法,罕涉理论。谶公所译,半属大乘,《华严》、《般若》、《宝积》、《涅槃》皆有抽译,隐然开此后译家两大派焉。同时尚有竺佛朔、支曜、康巨、安玄、康孟详、严佛调,皆各有译述。
二公以后之大译家,则支谦也。谦本月支人,汉灵帝时,月支有六百余人归化中国,谦父与焉,故谦实生于中国。而通六国语。支谶有弟子曰支亮,谦从亮受业,故谦于谶为再传。汉献末,避乱入吴,孙权悦之,拜为博士(谦本未出家)。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经数十种(《高僧传》称四十九种,《祐录》三十七种,《房录》百二十九种)。又注《了本生死经》。为经作注,自谦始也。所译虽多小乘(上列《大般泥洹》非今《涅槃》也。《安录》注云出《长阿含》),然《维摩》、《阿弥陀》两大乘经,此为首译(《房录》,《维摩》以康孟详本为首译,此为第二译,注云:两本大同小异。《祐录》不著康本)。而江左译事,谦实启之。
同时有颇重要之一人,则朱士行也。汉灵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般若小品》之旧本。士行谓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入西域。西行求法之人,此其首也。士行至于阗,果求得梵书正本,遣弟子弗如檀赍还洛阳,托无罗叉、竺叔兰二人共译之,名曰《放光般若经》,共九十品二十卷(卷数据《祐录》。今藏经本三十卷),即《大般若经》之第二分也。般若研究,自此日进矣。《房录》又载甘露七年有支疆梁接者,译《法华三昧经》六卷于交州。是《法华》亦以此时输入。然《祐录》不载,真否难断。
第一期最后之健将,则竺法护也。护亦名昙摩罗刹,系出月支,世居敦煌,故亦为敦煌人。护为西行求法之第一人,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实自护始。其所译,各部咸有:《宝积》四十九会,译得十六会;《华严》三十九品,译得五品;《般若》则译《光赞》三十卷,所谓《大品般若》者,此其首译也;而《正法华经》十卷,尤为《法华》输入之第一功。其他诸大乘经,尚三十余种,小乘将百种,大乘论、小乘论各一种(《祐录》载护公所译一五四部三〇九卷)。《传》称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又云:“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其志身弘法之概,可以想见。道安云:“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本传引)最能道出护公译风。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先后助护译事,时复加以润色。护没后,道真独译之书亦不少。
上第一期所出经虽不少,然多零品断简。所谓“略至略翻,全来全译”。实则略者多而全者希也。所译不成系统,翻译文体亦未确立。启蒙时代,固当如是也。
三
东晋南北朝为译经事业之第二期。就中更可分前后期。东晋、二秦,其前期也;刘宋、元魏迄隋,其后期也。
第二期之前期,罗什、佛驮耶舍、无谶接踵东来,法显、法勇(昙无竭)、智严、宝云,捐身西迈。大教弘立,实在兹辰。但吾于叙述诸贤以前,有二人当特笔先纪者,则道安及其弟子慧远也。安、远两公,皆不通梵语,未尝躬与译事,而一时风气,半实由其主持。安公弟子五百人,所至相随,后此襄译及求法者多出焉。其于已译诸经,整理品骘,最为精审。观前节所述经录,可知其概。翻译文体,最所注意,尝著“五失三不易”之论(详次节)。安公以研究批评之结果,深感旧译之不备不尽。译事开新纪元,实安公之精神及其言论有以启之。语其直接事业,则跋澄,难提、提婆之创译《阿毗昙》,实由安指导;而苻坚之罗致罗什,实由安动议。盖此期弘教之总枢机,实在安矣。安公倡之于北,远公承业,和之于南。远为净宗初祖,人所共知。乃其于译业,关系尤巨。遣弟子法领等西行求经,赍《华严》以返者,远也;佛驮见摈,为之排解延誉,成其大业者,远也;指挥监督完成两《阿含》及《阿毗昙》者,远也;在庐山创立般若台译场,常与罗什商榷义例者,远也。故诸经录中,虽安、远两公,无一译本,然吾语译界无名之元勋必推两公。
译界有名之元勋,后有玄奘,前则鸠摩罗什。奘师卷帙,虽富于什,而什公范围,则广于奘。其在法华部,则今行《法华》正本,实出其手。其在方等部,则《阿弥陀》、《维摩诘》、《思益梵天》、《持世》、《首楞严》诸经出焉,《宝积》诸品,亦为定本。其在华严部,则《十住经》之重译也。其在般若部,则《小品》、《放光》皆所再理。其在律藏,则大乘之《梵网》、小乘之《十诵》,皆所自出。然其功尤伟者,则在译论。论,前此未或译也,译之自什公始(同时佛念、提婆等译小乘论)。《智》(《大智度》)、《地》(《瑜伽师地》)两论,卷皆盈百,号论中王。《地》藉奘传,《智》凭什显。校其宏绩,后先同符。至其译《中》、《百》、《十二门》,因以开“三论宗”,译《成实》因以开“成实宗”,译《十住》因以开“十地宗”,此尤其章明较著者矣。计什所译经、律、论、杂传等都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据《内典录》)。而据后来梵僧所言,犹谓“什所谙诵,十未出一”。什之东来,实由道安献议于苻坚。坚至兴兵七万灭龟兹、乌耆以致之。及其既抵凉州,坚已败亡,安亦随没。越十六年而什方至。后秦主姚兴,礼为国师。在长安逍遥园设译场,使僧叡、僧肇、法钦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国立译场,自兹始也。什娴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乃更出《大品》(即《摩诃般若》),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什所译经,什九现存。襄译诸贤,皆成硕学。大乘确立,什功最高。
与罗什时代略相先后者,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昙摩耶合、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佛陀耶舍。跋澄、难提、提婆,及前耶舍,前后合力赓续译《增》、《中》两《阿含》及《阿毗昙毗婆沙》(小乘论),小乘教义,于兹大备。多罗、流支、罗又及后耶舍,则与罗什合译《十诵律》、《四分律》,律学昌明,实自兹始。罗又及后耶舍,皆罗什所尝师事也。而后耶舍,亦译《长阿含》,于是四含得其三焉。诸人多罽宾人,率皆小乘大师,唯后耶舍兼治大乘,什译《十住》,多所咨决焉。
其间有一人宜特纪者,曰竺佛念。佛念,凉州人,幼治小学,覃精诂训。因居西河,故通梵语。跋澄、难提诸人,皆不通华言,故所出诸经,皆念传译。苻、姚二秦之译事,除什公亲译者外,无不与念有关系。计自译业肇兴以来,支谦、法护虽祖籍西域,而生长中土,华梵两通;罗什以绝慧之资,东来二十年。华语已娴,始事宣译。故宏畅奥旨,必推三公。自余西僧,华语已苦艰涩,属文盖非所能,故其事业半成于中国译人之手。在后汉有张莲、孟福、严佛调、支曜、康巨、康孟详,在西晋有聂承远、聂道真、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在二秦则佛念。而佛调、二聂、佛念最著云。
东晋末叶,罗什誉望势力,掩袭一世。其能与之对抗者,唯佛驮跋陀罗。佛驮,迦维罗卫人,实与释迦同祖。智严、宝云西行求法,从之受业,因要与归。初至长安,与罗什相见,什大欣悦,每有疑义,必共咨决。未几以细故为什高座弟子僧祐、道恒辈所摈,飘然南下。慧远为致出关中诸僧,和解摈事。驮竟不复北归。法领从于阗赍得《华严》,法显从印度赍得《僧祇律》,皆驮手译。凡驮所译一十五部。百十有七卷。以较什译,虽不及三之一。然《华严》大本肇现,则所谓“一夔已足”也。
同时有异军特起于北凉,曰昙无谶。谶,中天竺人。初习小乘,兼通五明诸论。后乃习大乘。旋度岭东游,止西域诸国将十年,渐东至姑臧。值沮渠蒙逊僭号,请其译经。谶学语三年,乃从事焉。谶本赍《涅槃》以来,适智猛东归,亦赍此本。然所赍皆仅前分,于是复遣使于阗,求得后分。谶先后译为四十卷,则今之《大般涅槃经》是也。又译《大方等大集》、《金光明》、《悲华》、《楞伽》、《地持》诸大经,《优婆塞戒》、《菩萨戒本》诸律。其译业之伟大,略与罗什、佛驮等。
在此期间有一最重大之史的事实,则西行求法之风之骤盛是也。求法诸贤名姓及经历,具详前篇,今不再述。
其于译业最有密切关系者,则在其所赍归之经本,今略举其可考者如下:
法领——《华严》
法显——《方等泥洹》(即《涅槃》)《长阿含》《杂阿含》
《阿毗昙心经》《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
《弥沙塞律》
昙无竭——《观世音授记经》
道泰——《阿毗昙毗婆沙》
智严——《普曜经》《广博岩净经》《四天王经》
宝云——《新无量寿经》《佛本行赞经》
智猛——《大般涅槃》《僧祇律》
上述诸人皆通梵文,法显、无竭、智严、宝云、智猛皆有自译本,译学渐独立矣。
以上为第二期之前期。此期中之事业:(一)《四阿含》全部译出。(二)《华严》全部译出。(三)《法华》第二译定本出。(四)《涅槃》初出,且有两译。(五)《大集》译出过半。(七)【底本原文无(六)——校者注】《宝积》续译不少。(八)《般若》之《小品》、《大品》,皆经再治。(九)其他重要单本大乘经十数部。(十)律藏初译。(十一)大乘论初译,“空宗”特盛。(十二)小乘论初译,“有部宗”特盛。统而观之,成绩可谓至丰。佛教之门户壁垒,于兹确立矣。
四
南北迄隋,为第二期之后期。在前期中,经典教义未备,故学者之精力,全费之于翻译输入,若人之营食事也。及人本期,则要籍既已略具,学者务研索而会通之,若食后消化以自营卫也。故此期之特色,在诸宗之酝酿草创而不在翻译。其翻译事业,不过继前期未竞之绪而已。其译家之显著者,及其所译要品,略举如下:
求那跋陀罗《楞伽》《杂阿含》《众事分阿毗昙》等
(此公实应归入前期,故从朝代列此)
菩提流支《楞伽》《解深密》《思益梵天》诸经之再译,
《十地论》之再译,其他释经诸论
勒那摩提《宝性论》,其他诸论
佛陀扇多《宝积》诸品,《摄大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