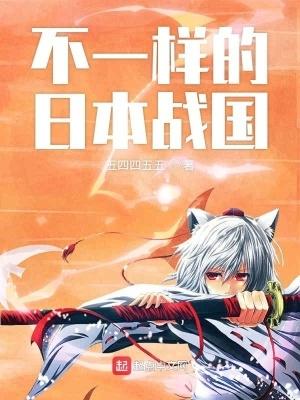腐书网>太好了啥意思 > 第46章 赌场10 双骰子(第2页)
第46章 赌场10 双骰子(第2页)
不等他说什麽,一声不合时宜的嗤笑插入,晏竖尔双手相交支在身前,下颌压在双手上,“航海家先生该不会是玩不起吧?输了要去找一位美丽柔弱又无辜女士的麻烦。还是说……这里面有什麽她知你知我不知的秘密?”
“……”航海家没看他,也没理会他的言语,只是定定地看了珍珠夫人许久却没有说什麽,他收回视线,最终只是道,“愿赌服输。”
“哗啦——!”
输方头顶的铁链按赢方押注的大小随之下降一定程度,一连串铁链声响起,铁锚有了下坠空间。
晏竖尔压了8枚筹码,铁链下降了一人高,离航海家的脑袋就差半个身子。他将手放在眼前比划,充满恶意地用两指捏出一个简短的距离。
他道:“看来航海家先生,您运气不是很好。”
後者闻言,“希望你能笑到最後。”
“我一定笑口常开,不劳您挂念。”晏竖尔回,他手心里起了层汗,面上却不动声色的挑衅着。
航海家,“希望如此。”
双骰子中,无人压7筹码归还,珍珠夫人用一杆木推推回筹码,接着向两人展示骰子,一如上次一般娴熟地掷起来骰子。
“请压注。”她指尖下意识敲击两下骰盅,看着两人。
鬓角微白的航海家睁开眼坐直了身子,看来晏竖尔那一席话比他想象中作用要大。
航海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骰盅,像是能将其看穿,然而这一次却是晏竖尔先压注,“压4,8筹码。”
他还是如上一轮一般压了8个筹码,如同被上一轮的胜利冲昏了了头脑,过于相信自己所谓的运气。
年轻人啊……
“压7,1筹码。”航海家紧随其後。
戴卯卯心底骤然涌上一股无端恐惧,她猛地攥住飞鸟,顾不得他那只手臂还受着伤,力度大到要抓进肉里。
她喃喃自语,“我有不好的预感。”
飞鸟警惕,“别乌鸦嘴啊你。”
下一秒,珍珠夫人打开骰盅,戴卯卯终于明白她在预感什麽——骰盅底下,两枚骰子加在一起,赫然是7。
“……怎麽会?”晏竖尔脸色苍白,不敢置信般喃喃自语,“不可能啊……”
这下轮到航海家笑,他笑起来皱巴巴,红棕色胡子抖动不停,像某个□□故事里所描述的怪人,“我说过,笑到最後的才是赢家,你还是太年轻,不懂得这个道理是时候该有人让你吃吃苦头。”
显而易见,这个人就是他。
他亲自动手拿起木推,将晏竖尔压下的8枚筹码收到自己近前,连带他自己压的1枚。这样一来他手里就有18枚筹码。
“真美丽啊——”航海家将这些筹码摞起,很高一串,最上端的因放置过于随意而摇摇晃晃,仿佛随时要掉下来。
反观晏竖尔,手边仅有两枚可怜的筹码,低垂着头一言不发整个人都快隐匿在黑暗中肩头时不时颤抖一下。
——或许是在软弱无能地哭泣。
珍珠夫人不关心局势,她只是笑问,“要开始下一轮嘛?”
“开。”
航海家擡擡手,她马上又一次娴熟地展示,舀起,晃动,指尖轻轻颤动。
“压2,全压。”
他推倒那座由他搭建的筹码塔,又如一开始般阖上眼,悠然地向後仰靠在沙发靠背上。
晏竖尔:“压7,全压。”
他也压上那两枚筹码,像是放手一搏,又像是死到临头的挣扎。
“开——”珍珠夫人毫不迟疑,擡手露出谜底。
她的声音拖的很长,长到让人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她的声音又很短,短的不过铡刀落下一瞬间。
航海家听到她说:“点数7。”
点数7。
不等他睁开眼调动视线去辨别真假,头顶铁锚骤然落下,就着他最舒适,最常做的姿势落在他腰间。
“咔嚓!”
铁锚扎进他身下的沙发,腥臭泛黑的血液喷溅射出,晏竖尔厌恶地盖住口鼻。
“喀……喀喀……”
航海家还没死,费尽气力地擡起头,双眼暴突如一只金鱼。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赌局,想说什麽,然而血块卡进喉咙,他已然没什麽好说的了。
对座少年施施然起身,擡手擦掉脸上血渍,冲着他露出一个灿烂笑容,“看来您才是没能笑到最後的那个啊。”
他不顾喷溅血液,靠近道,“听说,会赌的人不确定自己摇到了什麽点数时,可以将骰子摇在桌子旁边,轻轻地用手指敲击骰子,从声音和手感上判断点数。”
声音传到航海家耳朵里,轻的像是要飞起,“对,从刚开始我就知道你在出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