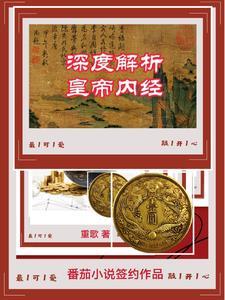腐书网>吾名玄机 > 第一百九十一章 别来无恙(第1页)
第一百九十一章 别来无恙(第1页)
“真是难为了你,成这德行了,还不忘诛邪!”
云仆走到这架破损凹陷得厉害的械人身边去,伸出手想像以往习惯的那样按在它肩上,可这械人骨架上下就没有一处能落掌的地方。
停顿了一会之后,云仆干脆将手放在牢房的另一边,轻轻地拨弄了下里面暗置的开关,“啪”的一声磁吸转了个极,原本被吸在上面的骨架械人落在了地上。
械人尚且有些茫然,但看着云仆的时候,空洞的眼眶里似乎找到了某个专注的点,一直跟随着。
“轻驰啊,本来你心思最纯粹,也无朝中任何势力插手。整个衙门司里,唯有你让老夫是最放心的,可你偏偏最后落成了这副模样。”
叶轻驰!
骨架凹陷进去的械人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不禁歪斜了一下头,似乎想从仅有的、错乱的记忆中寻找这个名字的印记。
云仆继续说着,“不荒山之行,诛邪司全军覆没,你身为流风营首领,难逃追责。可你现在这副模样,再大的责罚,无非当场诛杀,就像其他械人一样,最后投入这滚滚熔炉中,也就一了百了了。”
云仆的话,也不知道现在的叶轻驰能听进去多少,它只时而茫然,时而专注地听着云仆说话的模样。
就这样褴褛破败的骨架,任谁都不曾想象得到,在当初出发前往不荒山的诛邪的时候,流风营的统领,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而此刻,这牢房的顶
上,瓦片之间一只白猫踩着它的肉垫,无声地走过,在听到下面云仆的话音隐约传来的时候,白猫适时地停下了脚步,俯首朝着瓦缝间投下目光,无声地注视。
通过瓦缝间,白猫的瞳孔忽然一紧,在那双琉璃珠子一样的眼睛当中,映出了下面的场景。趴伏着茫然地跪着的械人,头颅和身上凹陷的凹陷,损毁的损毁,不是她阿叶,又是谁!
而在凹陷损毁的械人旁边,云仆仍旧看着它,言语中似乎也带着踌躇,不知该将如何处置。
“诛邪司,可是诛邪的啊,你何苦自投罗网呢!”云仆说道,轻叹了一声,“芯片也彻底损坏,谁都没法修复,你便在外自生自灭也罢,何苦来哉。”
“你叫我,如何处置你好呢?”
白猫听到这话的时候,不觉将两对尖牙紧咬,不觉又将肉垫里藏着的爪子亮了出来,剑拔弩张,做出随时要冲下去抢人的模样。
然而,下方的凹陷机械却机械性地,似乎在痛苦又极力地寻找回属于自己的记忆,最后顿挫般地开口。
那破烂的骨骼下颌,还在不断地张合着,但就这样张合了许久仍旧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正确来说是不知道该发出什么声音,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说什么。
最后,只有依旧重复着那两个字!
“诛邪!”
“诛邪!”
“诛邪……阿叶诛邪!”
阿叶,要诛邪!
见着叶轻驰这架械人如此模样,在上面的小白
猫愣住了,就连云仆也愣住了。
许久之后,云仆终将那只手搭在了那颗凹陷进去的头上,奇的是,云仆的手触碰到它头上的时候,它安静了下来,犹如最虔诚忠诚的仆人。
安静了许久,云仆长吁一口气,“到这地步了,还心心念念着诛邪,也罢!”云仆说罢,转身朝外走去。
“那你就收拾收拾,随着他们一起出任务吧!”
……
泗水渠日复一日的浑浊,一日更比一日甚。
这是玄机踏着小船靠了岸之后的第一感觉,甚至,这弥漫在空气中的恶臭味,要比前些天离开的时候还要难闻。
真的难以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如何熬过这一天比一天还艰难的日子的。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最大的难处不在于这恶劣的环境,更在于这里的贫穷,他们牺牲自己,甚至下一代的健康,在那些排出的污水里,一代一代地在此沦陷和腐烂。
这里就像是地下城散落在外的一座座小作坊,用以勉强养活这里的人。
水岸边上,年迈病重的老妪披着粗重的麻布,身上已经溃烂得不敢见人了。在看到有人登岸的时候,更是紧紧地捂紧了身上的麻布,低下了本就佝偻的身姿。
寇占星在来之前,却说有点东西要买,于是半途转道离去,让玄机和霍青鱼两人先行。
“他怎么了?”霍青鱼不知道寇占星心里对这泗水渠有所别扭,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点想避开这里的
感觉。
玄机看着寇占星一路狂奔着离去的背影,轻哼一声,“从他身上,我几乎可以看到当年寇天官是什么样的人。”
玄机没有继续往下说,霍青鱼却更加疑惑了,这和寇天官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