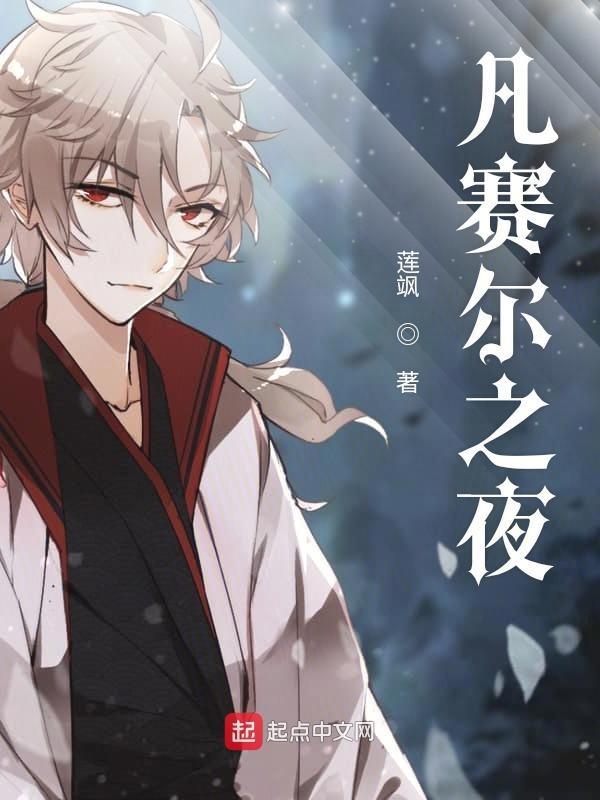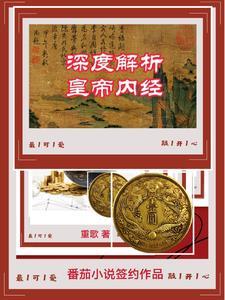腐书网>我所行之地歌词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你倒是操心上这些了,买多了的话就跟你先前买的珠玉簪子放在一起,要是有差池……”李融话音还未落,苏肆就继续接上了下半句,“公子怎么还记着这件事,要是有差池我就再讨不到媳妇。”
李融轻笑着嗯一声,看苏肆忙前忙后拉着店家问款式和价钱。他自己也乐得一个人在一旁细细看过,阿娘惯爱花草的样式,又不喜浮华的颜色。看了良久才选定一支,中间也被苏肆拉着看过他选出来的款式,于是又在其中指了两件由店家包进木匣中装好。
至于木梳的样子却都相差无几,只是所用材质不同。李融便指了阿娘用惯的颜色,一一听店家讲过材质。檀木江南为佳,长安铺中所陈列出来的自然不如金陵姑苏那边的。跟苏肆交谈过,选定了黄杨木做的齐梳。
木匣中放了明黄的衬布,大概是店家的传统。看上去大体也和木梳本来的颜色相互映衬,李融便没叫店家换成素色。
苏肆拿好包袱将木匣抱在怀中,李融付定了银钱走在他后面一些。“果然长安的东西就是很贵,不过公子的眼光向来好,到时候老夫人一定会喜欢。”
他听到这话只是笑笑,“许久不见阿娘了,回去定要怪我们离家太久,那时不知怎么安慰才好。”苏肆也有同感,“还好老夫人更担心公子,我呢,就算个添头,不至于让老夫人怪得那么久。”
“等阿娘回过神来就该轮到你了。”李融答过苏肆这番话。他们从长街尽头绕进巷中,这边的行人就更少了。楼阁相接,虽不像金陵城中处处红木,却也能看出来所用木料非俗品。大多也都顾着自己行路,大多都有门仆站在两旁守着府邸。
缀着的琉璃瓦亮着光,偶有装饰严正的马车停下,待府邸的主人回来后,两扇刷着红漆的大门便紧紧闭上。李融慢慢认过牌匾上的字和自己印象中的官职一一对应,正欲开口相问,却想起走在自己旁边的是苏肆,而不是前几日一直在的薛珩,只好作罢。
苏肆小声念叨着木料或是其上的金银镀色,不断心算着价钱,李融也算乐意听他算出来的银两。忽然觉得长安极盛的繁华算得上奢靡,建造府邸所用的价格比苏肆现在能脱口而出的数字只多不少,更遑论其中吃穿用度。
长安的街巷勾连盘折,几乎不会有绝路的时候。他们走进巷子深处的时候便又进到另一条熙攘的长街里去。长街上摆着摊位的商贩几乎和刚才如出一辙,不是些孩童喜欢吃的甜食,就是璎珞簪子一类,还有善杂技者敲锣在街旁围在人群里表演。
李融自己对这些兴趣不深,奈何自家书童非要挤进去。周围嘈杂声响在耳边,等敲锣声再响一遍的时候,李融还是没想起来刚才究竟看了什么,只是等手捧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多摸了两枚铜钱放进去当作捧场。
方及正午街上的人又涌进附近的酒楼茶楼中,李融索性留下苏肆等待想吃的饭食,自己则先带着木匣回了客栈歇息。入冬的长安是比庐州要冷,但是经半天在人群中挤搡身上倒暖起来。
登上楼梯的时候店内的伙计也都在忙着准备饭食,李融捧过所买的木梳和簪子先进了厢房中。他在开门的时候瞥了一眼对侧,薛珩所选的厢房门还紧闭着,桌上的油灯还没有熄灭,隔着薄绢隐约能看到四处倾斜的光影。
他先安置好了木匣,将其中能装进自己放绢书的木盒中的也都一一收拾进去,多一层木匣总会避免一些突发的磕碰。店家没来得及换上新茶,李融抿过有些微微放凉的茶,余在口中的苦涩更添几分风味。
他想起从竹卷中窥得的长安来,那是前朝的都城,也是今朝的都城。不仅有长街一如既往的日日繁华,也有或是兵不血刃,或是尸横遍野的刀剑相接。即使对于现在的他还算无关之事。他却禁不住去想,天下寰宇,如自己游学所历,便是万里山河,其中人群往来,却是众生百态。于高官王侯,一生便在殿内府中徘徊,又或许踌躇着,或许面带豫色。
李融又止住这般思绪,君臣之间于礼不可僭越,于德不可妄论。他记起曾经夜谈阿父所慢慢教自己的道理,记起日日诵读夫子所讲学的儒道圣贤,甚至想起临沂论道那夜但笑少言的薛拙之。
他觉得半年快过,自己已经从庐州游学至了王都长安,为官为政之道,即使再有踟蹰却总在心里有所择定。可他又觉得自己几乎要跨不过那道踟蹰来,他很难维持一方笼罩在江南那般的安宁之下,他也不愿见到任何一地如年年的颍川,大水为患,忧心仓中有粮或是无粮。
李融歇了这般挂念于心肠的念头,躺在榻上一遍遍去读他曾经记下的未解的路,回到他之前经年所熟悉的典籍中,在自己所寻求的表面的安宁中睡下去。
梦中隐约能听到对侧的房门开合的声音,却不知道薛珩是回来,还是远去了。李融在梦中重见近日所看到的北地巍峨的山,远处起伏的山顶上落下一抹抹白,那是他还未等到的长安的雪。他也再见到江南缓和的水,即使入冬之时也照常汩汩流动着。他却不愿再梦中原浑黄的土地和决堤的大水,不去再见裸露的白骨和那双沉默而浑浊的眼睛,以及他们对放粮来熬过这个冬天的一遍遍喃语。
长安的月随着日愈凛冽的寒风渐渐变圆,悬在云层之上隐下尖锐的缺角。泛起的银光洒在灯火不休的城中,长街便总是一半月色,一半熙攘。李融陪着苏肆逛了四五日,才算走尽了长安城的街巷,其中弯绕苏肆还是没能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