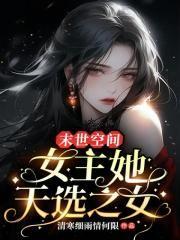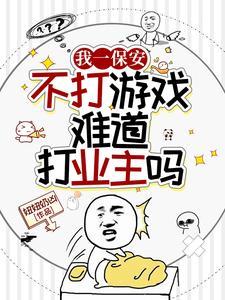腐书网>八零军婚甜蜜蜜徐子矜陆寒洲 > 第43章 婆媳联手(第1页)
第43章 婆媳联手(第1页)
煤油灯的光晕在土墙上晃出暖黄的圈,苏晚晴的毛背心织到第七排时,婆婆突然放下纳到一半的千层底,指尖划过领口弧度:"太低了,"她的银顶针磕在竹篾织的线笸箩上,出清响——那是用顾沉舟父亲的弹壳磨的,内侧刻着"o",正是顾沉舟参军的日子,"寒风吹脖子,比子弹擦过还难受。"
苏晚晴望着老人鬓角的白,突然想起顾沉舟说过,母亲在父亲牺牲后,靠给边防连织毛衣供他读完军校。此刻婆婆的毛线针在指间翻飞,拆衣的动作利落得像在整理作训服的褶皱,拆下的蓝毛线团里,还缠着几根银线——那是从顾沉舟退役的防弹衣上拆的,专门用来加固领口。
"当年你爹的毛衣,"婆婆的针脚突然密了三倍,形成道整齐的竖线,"领口都是按部队队列的间距织的,"顶针在毛线里划出冷光,"每寸十二针,"指了指自己织的毛领弧度,"和边防连的防风墙一个角度。"
月光漫过窗台,照见苏晚晴的针线筐里躺着半片红景天——她原想在领口绣弹道抛物线,此刻却盯着婆婆手中重新起针的毛领,突然想起老人床头的旧相册:二十年前的冬天,婆婆抱着年幼的顾沉舟,膝头堆着给边防连织的毛袜,每只袜跟都绣着极小的五角星。
"娘,"她摸出从空间物资取的、用红景天染的金线,"在领口内侧绣朵菊花吧,"指了指婆婆围裙上的补丁,那里用碎布拼了朵小菊花,"您最爱的花。"
婆婆的毛线针突然停顿,顶针内侧的弹壳刻痕映着煤油灯的光。她想起丈夫牺牲那年,顾沉舟在烈士墓前摘的野菊花,夹在父亲的日记里,花瓣早已褪色,却在每页边角留下浅黄的印。"菊花耐霜,"她的声音轻下来,"就像军人的妻子,"指了指苏晚晴腕间的弹壳手链,"经得起风寒。"
两人的影子在土墙上交叠,苏晚晴的弹道抛物线针法与婆婆的队列式针脚在毛背心上相遇:领口的可拆卸毛领用银线织成锯齿状,是婆婆按战壕掩体的弧度设计的;内侧的小菊花用红景天金线绣成,花瓣末端缀着极小的弹壳图案——那是苏晚晴用顾沉舟年雪崩时的弹壳粉拓的印。
"当年沉舟第一次寄军功章,"婆婆突然摸出藏在毛线团里的、顾沉舟的第一枚弹壳,底缘刻着"o","我就知道,"顶针划过毛背心的加固线,"他的领口,"望向苏晚晴正在绣的菊花,"得有两个女人替他挡风。"
缝纫机的咔嗒声从隔壁传来,苏晚晴突然想起顾沉舟的作训服袖口,总留着婆婆补的耐磨补丁,针脚是工整的"人"字形,而她绣的弹道抛物线,总在补丁边缘轻轻环绕。此刻的毛背心,银线毛领像道钢铁防线,金丝菊花则是防线后盛开的温柔,正如婆媳二人,一个用军人的严谨织就铠甲,一个用军属的细腻缀满花香。
"试试合不合身。"三天后,顾沉舟刚推开"舟晴园"的门,就被婆婆递来的毛背心套住脖子。他摸着领口的银线毛领,现内侧的菊花绣在左胸位置,恰好贴着心脏——那里藏着他父亲的烈士证复印件,还有苏晚晴缝的、写着"平安"的草药包。
"领口的弧度,"他的指尖划过锯齿状边缘,突然想起边防连的防风工事,"和狙击镜的腮垫角度一样。"喉结在毛领里滚动,目光落在菊花的金丝上,那抹红恰如母亲当年别在他书包上的、晒干的野菊花。
苏晚晴望着他红的耳尖,知道他现了毛背心的秘密:银线来自他退役的防弹衣,金线染着她新研的、能驱寒的红景天药剂,而婆婆的针脚里,藏着二十年前就开始的、对军人后代的守护。
暮色漫过晒谷场,婆婆的千层底在毛背心旁泛着暖意,鞋底的弹道线与毛领的锯齿纹,在月光下连成串光的印记。苏晚晴突然明白,婆媳联手织就的,从来不止是件毛背心——是用两代人的爱与坚韧,编的甲,既能挡住边疆的风雪,也能守住心底的温柔,让那个总在靶场流汗的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家的温度。
这一晚,顾沉舟的训练日志写在毛背心的毛线球上,字迹沾着红景天香:"母亲的针脚是第一道防线,妻子的刺绣是第二道温柔。当毛背心的银线毛领挡住寒风,内侧的菊花贴着心跳,突然懂了:军人的后背,从来不是单枪匹马的守望,是两个女人用毛线与弹壳,织就的、永远温暖的港湾。"页脚画着毛线针与弹壳顶针,中间是重叠的"舟晴"二字,像两簇在寒冬燃烧的火,一簇传承着母亲的守望,一簇绽放着妻子的柔情,共同守护着,属于这个军人家庭的、永不褪色的温暖。
喜欢八零军婚甜蜜蜜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军婚甜蜜蜜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清寒细雨情何限末世空间:女主她天选之女
- 末世这么神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