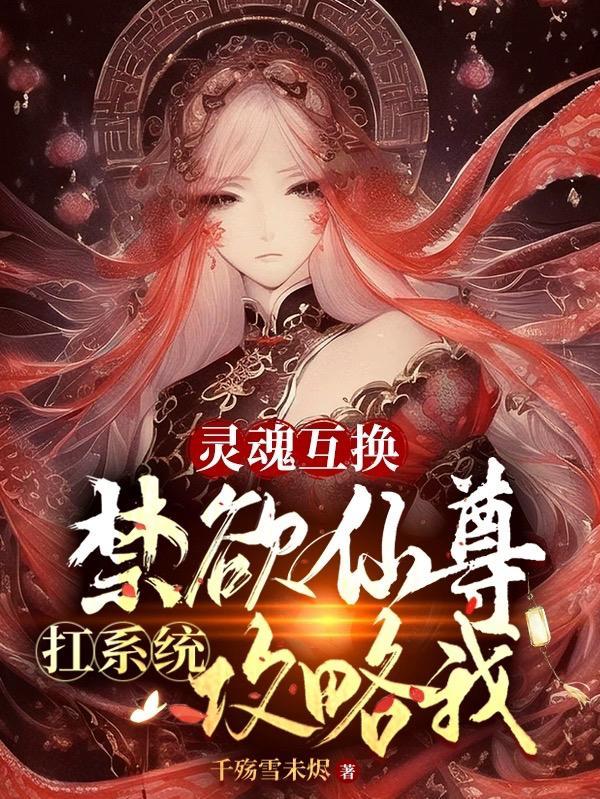腐书网>女人中的女人雌性中的雌性是什么意思 > 第87章 不好惹(第1页)
第87章 不好惹(第1页)
从坐上客车一直到提着编织袋等在月台上,兰舒都晕晕乎乎的。
高兴,确实高兴,兰舒这辈子都没这么高兴过。
她伸长了脖子望着那列吐着白气缓缓进站的绿皮火车,一颗心像揣了只兔子,紧张又兴奋。
她甚至能听到自己“咚咚咚”狂跳的心跳声,原来火车真的和电影里演得一样,好长好长,而且还一节一节的像一条绿色的大蟒蛇。
火车刚停稳,“哗啦”一下,人群如潮水般涌了上去。
兰舒紧紧地攥着车票被裹挟在其中,随着人群往车厢门涌动,耳边全是乱糟糟的声响,震得她耳朵疼。
“让一让,让一让!”有人扯着大嗓门喊。
兰舒不知道被谁摸了一把屁股,再回头时根本找不着人影,所有人都死命往里挤,这时候问没人会承认的。
兰舒咬着牙大吼了一句:“哪个手爪子欠的,浑身上下长烂疮!出门让车撞死都没人给你收尸!”
这一吼,周围两米开外都安静了下来。
有人不满地小声嘀咕:“姑娘家家的咋说话呢”
“就是的,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兰舒瞪过去,“又没指名道姓的骂你,咋的?刚才是你手欠摸我屁股啊?”
对方赶紧辩解:“你可别诬陷,我离你那么远呢,手可伸不了那么长!”
“那你在那没事捡骂干什么?骂谁谁听着,没骂你就消停待着得了!”
对方不服气地撇了撇嘴,不再接话。
兰舒一骂完,明显感觉身后原本推搡自己的人都自动收回了手,还往后站了站。
其实她也不是戾气重,一个小姑娘自己出门在外,要是想不吃亏就必须得摆出一副悍妇的架势。
她不找事,但也绝对不会让别人占她一点便宜。
大部分人都是欺软怕硬的,她长得好看更容易让别人多看几眼,所以她必须“不好惹”,才能保护好自己。
况且她越来越现,“不好惹”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之前她“好惹”,也没见别人对她有多尊重多优待。
自从她成为了一个“不好惹”的人之后,全世界都给了她好脸色。
列车员原本在车厢那头忙着疏导人群,听到这边的动静,扶了扶帽子,远远地瞥了兰舒一眼。
他抬起手指着后面的方向大喊道:“都别挤啊,一个接着一个上,有什么好挤的!只要买了票的都能上车,大家都别着急!”
列车员话了,可疯狂的人潮依旧汹涌。
不少人依旧像没听见一样,仍拼了命地往前面挤,但兰舒这边却清静了不少。
刚才还在她身边推挤的人群,此刻都自动和她避开,没人愿意贴着她走,生怕不故意碰她一下就得挨她一顿狗屁呲。
兰舒乐得自在,慢悠悠地站在队伍里跟着人群一小步一小步地往车厢门的方向蹭。
好不容易挤到车厢里,一股混杂着汗臭、烟草味和饭菜香气的怪味扑面而来。
她皱了皱鼻子,还是被这新奇劲儿盖过了。
在狭窄的过道里,她费力地挪动脚步,一边躲避着四处横飞的行李,一边按照车票上的信息寻找自己的卧铺。
“号上铺,号上铺……”她嘴里小声念叨着,目光在床铺的编号上一一扫过。
列车员正沿着过道巡回检查,听到兰舒的嘀咕,停下脚步抬手往后指了指:“号还要往前走七八米,看清铺位啊别走错了。”
兰舒感激地回以微笑,道了谢,按照指示,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床铺。
到了之后兰舒看了一圈,地上都是其他乘客的行李,她想着包里也没什么贵重物品,便顺手将自己那略显破旧的编织袋,费力地塞到了下铺的床底。
靠近她这边的下铺坐着一位年轻的母亲,床上还有个看起来三四岁模样的小男孩。
男孩正啃着一个削了皮的大苹果,每咬一口,嘴里就用力往外喷吐苹果碎屑,残渣溅得到处都是。
见兰舒把行李塞到了自己床下,年轻母亲眉头瞬间拧成了个疙瘩,满脸不耐烦地斜瞥了她一眼。
兰舒还以为对方要说什么不好听的话,结果女人也就是瞥了那一眼,随后便又若无其事地拿起手绢,继续给孩子擦嘴。
车厢里很快人满为患,空气愈憋闷。
兰舒不想这么早就爬上那又窄又闷的上铺躺着,便踱步到窗边,等火车启动了好好欣赏一下风景。
一切安顿妥当,她这才有闲情打量起车厢内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