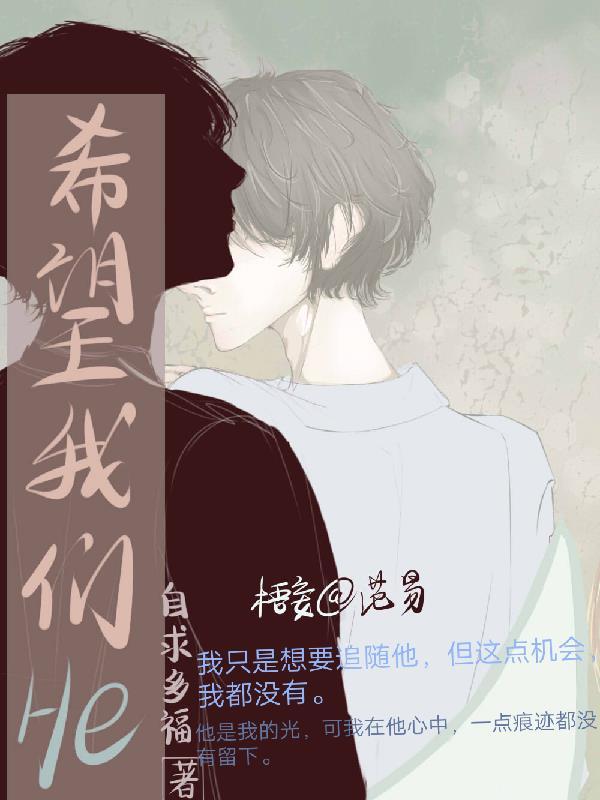腐书网>猫哥在上TXT百度 > 第49章 续49 故事(第1页)
第49章 续49 故事(第1页)
程然后来这么窝着躺着也便跟着睡着了,不过因为之前睡了太久,这次没一会儿便再次醒来,睁眼的时候猫哥还搂着他睡得正熟。他微微仰了仰脸望着近在咫尺的猫哥,目光从那熟悉的眉眼滑落至两颊颏角上细细密密的络腮胡上,望着望着,垂下头往猫哥怀里靠了靠,觉得之前心里空了的那一小块就这么被填满了。
之前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事情就这么稀里糊涂理所当然地过去了,好像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跳过了中间相隔的那几年,谁也不去提,谁也不去谈。但有些事终究还是不可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过去,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处理完,两个人的状态也都恢复得差不多,到底还是要谈谈。
只不过程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怎么谈。
于是他坐在酒店房间落地窗前的沙发上,望着刚冲完澡背对着他在收拾衣服的猫哥,目光从他身上挪到一边,又挪回去,来来回回不知道挪了多少回,却始终没出声。
但他这略带犹疑的目光还是太明显了。猫哥被他这么看来看去,到底还是很轻地笑了一下,收拾完东西之后转过身来走到程然面前蹲下,用一个微微仰视的角度望着程然,轻声问:“怎么了?”
程然看了他一眼,又往一边挪开了目光,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用了一个最老套的话语:“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其实都是废话。程然这会儿彻底清醒了之后便有了些原本没有察觉到的尴尬,之前没压抑住的一些情感也都再次回到了皮囊之下,安安分分地藏好了。两人那么久没见,到底还是因为间隔的那些时日有了些微的隔阂与疏远,连聊天都一时半会儿不知该怎么聊,客套得厉害,用的全是寒暄之词。
猫哥笑了笑,应了一声说:“酒店前台,工作不算特别累。”
程然看了他一会儿,最后还是犹犹豫豫地问:“不做网黄了?”
“嗯。”
程然看着他,安安静静地,似乎在用目光询问他为什么。
猫哥垂下眼,很轻微地笑了一声,说,他本来就不喜欢做这个。
既然不喜欢,那为什么之前还要做呢?程然想问,但话语在舌尖转了一圈,终究还是咽回了肚子里,最终问出口的是另一个问题,问猫哥生活上怎么样,还好吗。
猫哥看着他的眸子,唇边挂着很淡的一抹笑意,说:“我还是一个人。”
程然愣了一下,心道我不是想问这个,便又听见猫哥接着道:“我一直都很难喜欢上一个人。但一旦喜欢上了,就很难忘记。”
程然张了张嘴,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他吸了口气,垂了垂眼,心里没来由地有了些怒意。他在心里一句一句地质问猫哥,问他既然承认了喜欢,为什么那时候还那么坚决地要走,那么突然、那么不留余地,后来一点消息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走了之后现在还来跟他说这些,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他想怎么样。
一句一句质问抛出来,带着连他自己都能轻易察觉到的怨气。
但他也仅仅是这么在心里无声地质问着,目光落在虚空中的某处,始终沉默,脸上神情甚至都没什么变化。
猫哥没有等到回应,自嘲般地笑了一下,也撇开了目光,问他怎么样,过得还好吗,是不是要毕业了。
程然应着,说他七月上毕业典礼,很快了。
猫哥笑着应了一声,似乎还想问为什么,被程然打断了。
“罗一成喜欢我。”程然声音里没什么情绪,仿佛只是随口一提,“你是不是知道。”
后面那句的语气是肯定的,因为他知道猫哥知道,而他只是想让猫哥知道他知道猫哥知道。
猫哥默了一下,说:“是。”
程然的目光落在房间的地面上,沙发底下铺了一层地毯,色彩很深,样式很旧。“你当时……”
“不是。”程然话都没说完,就被猫哥打断了。
程然的目光从地毯上抬起来,落到猫哥的脸上,依然没什么情绪,但却仿佛在明明白白地表示他不信。
猫哥同他对视了一会儿,说:“他很好,我确实想过如果你们可以在一块儿,会很好。但当时确实和他没关系——和任何人都没关系。我只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
程然的目光又移开了,落在略显暗沉的地毯上缓缓描摹着旧时流行的大花图案,轻声问:“什么坎?”
猫哥的目光也跟着他落到地面:“网黄。太脏了。”他忽然笑了一声,“你太干净。我配不上你。”
程然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下文,便扭头看着猫哥,看了半晌,终究还是没能按耐住那个他困惑了很久很久的问题:“你那么厌恶做网黄,当初又为什么要做呢?而且我记得,你说你做了很多年。”
猫哥依然垂眼望着地面,很久都没有反应。程然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却忽然听见他轻嗤了一声,说:“那时候年轻,幼稚,叛逆。”
这三个词说完,猫哥又没声儿了。半晌,他偏了偏头,看见程然静静望着他,便笑了笑,问:“你想知道?”
程然垂了垂眼,未置可否。
老酒店的房间装潢铺满地毯,于是当他们都陷入沉默,房间里便是让人几乎丧失五感的静寂。毛茸茸的织物吸收音波,也钝化了所有知觉。程然在这样令人沉溺的环境中浸着浸着,慢慢地,听着猫哥给他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主角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有些人会习惯于称呼那样的家庭为“高知”,在他们面前本能地就带有一丝尊敬。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被母亲牵着出去玩,在楼梯上遇见邻居,对方都会很浅地俯身或是点头,称他母亲一声老师。其实他到现在都不太知道该如何形容他的家庭,如果用最简单的两个字来概括,应该就是体面。
父母体面,家庭体面,于是这个小男孩从小就学会了要和家人一样体面,也从小就是最受大人喜欢的那种孩子——懂事、乖巧、省心,成熟得不像是那个年纪的小孩。他聪明,优秀,还漂亮,从小学开始,所有的老师都夸他情商高、自觉、独立,形象又好,于是各类奖项与比赛都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而他也稳稳当当地接下所有,每一次都能不负众望地拿到最好的结果。老师们都喜欢他,也喜欢他的家人,觉得他成绩好能力强模样也好,觉得他的父母省心地位又好。所以后来很多次,他自己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完下台,便与自己作为家长代表发言的家人擦肩而过。
所有人都夸赞他、羡慕他,身边的同学见到他的父母,都会叹一句这出众的气质。但其实回到家里,回到那个所有人都称赞的家庭里,这个小男孩便再也得不到一句称赞。
他可以从所有熟识或是陌生的人们口中获得大把的赞誉,却从未从自己的父母口中听到过一句夸奖——因为他们永远都觉得他不够好,他可以更好。
他拿了班级第一,父母问他为什么不是年级第一。他拿了年级第一,父母说一次第一不能说明什么。模拟考区定位他拿了百分之一,父母跟他说他学校在教育大区,学校多升学容易,但是人少,如果放在新区几万考生的定位里、在全市统一的大定位里,他又有多少竞争力。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母是体面人,他们从来不会打他骂他,连红着脸高声一句责骂也少见;但他从他们口中听到最多的便是否定,各式各样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