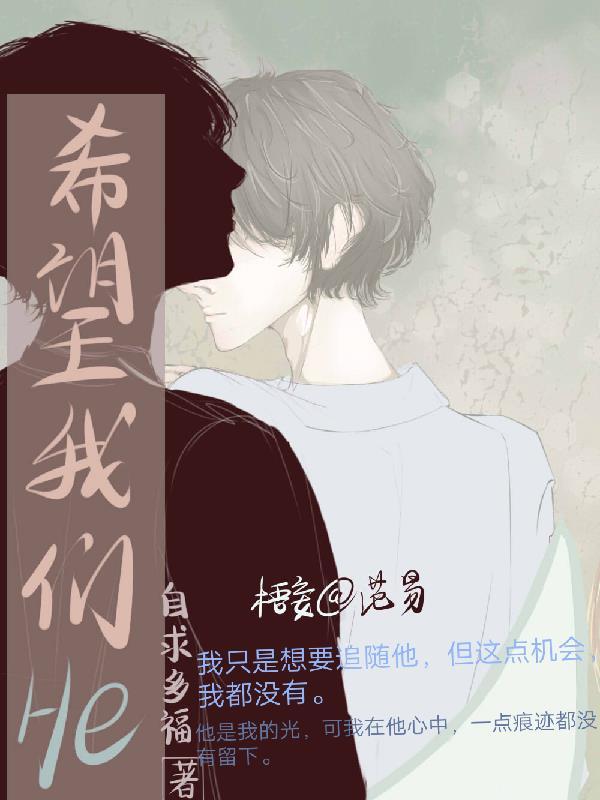腐书网>重生之安陵容视频 > 第88章 逢宿敌隐暗潮(第1页)
第88章 逢宿敌隐暗潮(第1页)
惊逢宿敌隐暗潮
安陵容手颤着放下茶盏,一夜未眠。那竹梆声似魔咒缠心,她满心忧惧。烛火摇曳,映着她憔悴的脸。
晨光漫过雕花窗棂时,安陵容正用银簪拨弄着青瓷盏里的杏仁片。
昨夜三长两短的竹梆声在耳畔挥之不去,像是有人用钝刀在骨头上刻下印记。
宝鹃端着铜盆进来,盆沿凝结的水珠坠在地上,洇出个歪斜的八卦形状。
"娘娘可要传早膳?"宝鹃的声音惊醒了梁上燕子,翅膀扑簌簌扫落几片金粉。
安陵容望着铜镜里模糊的面容,镜面忽然映出窗外一截茜色裙裾。
夏常在扶着宫女的手走过廊下,鬓边鎏金步摇在朝阳里晃出刺目寒光。
那目光犹如淬毒的银针,隔着窗纸都能觉出几分阴冷。
"今日去景仁宫请安,穿那件藕荷色云锦袍。"安陵容指尖抚过妆奁里的羊脂玉镯,前世夏冬春被赏一丈红的惨叫声突然在记忆里炸开,激得她腕间起了一片粟粒。
御花园的夹竹桃开得正好,殷红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溅开的血珠。
安陵容驻足观赏池中锦鲤时,忽听得假山后传来刻意压低的嗤笑:"都说贵妃娘娘是观音菩萨转世,怎的华妃娘娘前脚刚进冷宫,后脚钦天监就占出大凶之兆?"
夏常在涂着蔻丹的指甲掐断半朵芍药,染着花汁的指尖指向这边:"要我说啊,这宫里最会蛊惑人心的,怕是某些吃斋念佛的"
宝鹃气得要冲过去理论,被安陵容用团扇轻轻拦住。
水面浮着的残花突然打着旋沉入池底,她瞥见夏常在绣鞋上沾着的几粒香灰——正是宝华殿特供的檀香。
皇后今日戴着串新制的碧玺佛珠,翡翠替换了断裂的玉珠。
当夏常在故意打翻茶盏弄污安陵容衣摆时,十八颗碧玺恰巧滚过乌木地板,在晨光里折射出蛛网般的绿芒。
"臣妾该死!"夏常在跪得笔直,眼角却斜飞着望向主位,"听闻贵妃姐姐最是慈悲,定不会为件衣裳怪罪妹妹。"她腕间赤金镯子叮当作响,竟是华妃旧物。
安陵容接过绘春递来的帕子,慢条斯理擦拭着衣上茶渍。
帕角绣着的合欢花浸了水,花瓣纹路渐渐显现出暗红丝线——与昨夜砖缝血迹如出一辙。
她抬眼看向皇后,现对方正盯着自己染红的指尖。
雨是申时开始下的。
安陵容倚在窗边翻看《地藏经》,忽见夏常在的贴身宫女抱着油纸包匆匆穿过雨幕。
那宫女在转角处脚下一滑,包裹里滚出个扎满银针的布偶,朱砂写的生辰八字被雨水晕开,依稀能辨出"戊寅癸亥"等字。
宝鹃撑伞追出去时,青石板上只余几缕猩红线香。
安陵容蹲身抚摸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前世冷宫砖缝渗血的记忆与眼前景象重叠,恍惚听见白绫勒紧脖颈时的吱呀声。
"娘娘,端妃娘娘送来的安神香。"小宫女呈上珐琅盒时,袖口沾着片夹竹桃瓣。
安陵容揭开盒盖,见香丸下压着张裁成莲花状的黄纸,朱砂绘的符咒在烛火中忽明忽暗。
更漏滴到戌时三刻,窗外又响起竹梆声。
这次是两短三长,伴着夜枭嘶哑的啼叫。
安陵容推开西侧窗,恰见夏常在的暖轿消失在宝华殿方向,轿帘缝隙里垂下一缕明黄流苏——那是唯有亲王福晋才能用的规制。
雨夜惊雷劈开云层时,安陵容正对着铜镜梳。
镜面突然蒙上雾气,待她伸手擦拭,赫然照出端妃苍白的脸孔立在身后。
转身刹那,妆台上烛火骤灭,唯有那盒安神香在黑暗里泛着幽幽青光。
铜镜里端妃的面容被烛火割裂成阴阳两半,安陵容搭在妆台上的手指微微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