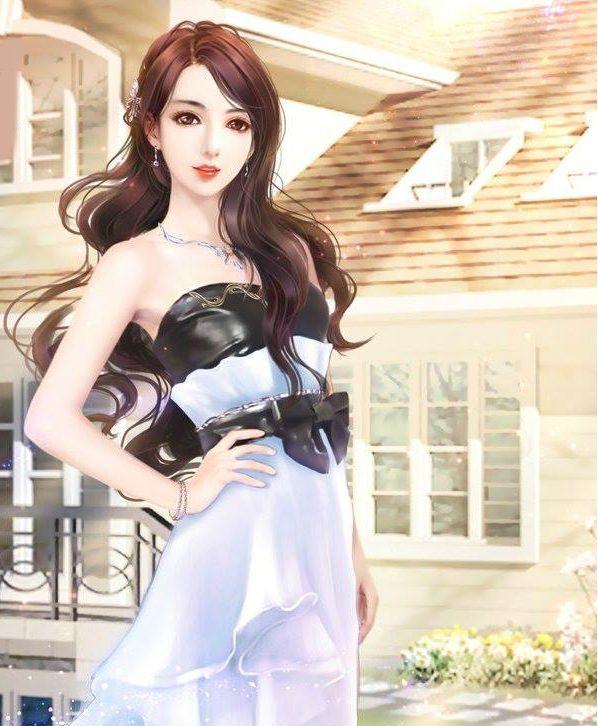腐书网>贵妃二嫁txt起跃 > 第38章 变故(第3页)
第38章 变故(第3页)
鸣春也被动静声吵醒了,早披了衣裳出去,吩咐人到前院打听消息,回头见韩千君也起来了,忙取了一件斗篷披在她身上,“娘子先别着急,醒冬去问了,许是老夫人又在同夫人闹呢…”
话没说完,醒冬回来了,手里提着灯盏脚步走得飞快,到了韩千君跟前,脸色发白,惶惶地道:“国公爷今日去了大理寺,人还没回来…”
韩千君一愣,“什么叫没回来?”没差人回来送信吗?
醒冬又颤抖地道:“世子爷,二爷,三公子,都没回来…”
韩千君脸色一变,衣裳也没来得及换,一面走一面把肩头的斗篷系带系好,接过醒冬手里的灯盏,快步往前院赶去。
郑氏还是白日的那一身,压根儿就没睡。二少奶奶也来了,两人一前一后立在院子里,不停地派小厮出去打听消息。
韩千君从廊下匆匆赶来,正好小厮在禀报消息,不由放轻了脚步,竖耳去听,“夏季的几场大暴雨,好几处宫殿都漏了水,二公子今日一直在工部,对照着图纸在规划如何修缮,快下值时,户部来了人,说有一处工程的款项要找他核对一二,人是跟着户部侍郎离开的,工部的人可以作证,离开的时辰乃酉时末…”
“三公子今日在翰林院纂修一本史书,下值得晚,酉时末才离开,有人见其马车出了翰林院,但没出宫…”
又是酉时末。
韩国公去大理寺的时辰也是酉时末。
这是有人精心策划出来的一场抓捕,把国公爷连同他的儿子们一道给控制住,谁也救不了谁。
六年前,郑氏便曾见过一回风雨,面色还算镇定,可二少奶奶到底还年轻,新婚半年不到夫君便出了事,急红了眼眶,见韩千君来了,走过去抓住了她的手,身子都在抖。
郑氏看了韩千君一眼,也没问她怎么来了,继续问小厮,“世子呢?”
小厮道:“世子午后便出了大理寺,人今夜在城外。”
好一招调虎离山,把国公府的人一个一个分散开,再来行事,看来秦家的案子,已经挖到了最关键的东西了。
“堂堂一品国公爷,朝廷命官,在天子脚下突然不见了人,去了哪儿,谁带走了,总得有个去处,大理寺没人,便去问锦衣卫,锦衣卫没见到人,便去慎刑司问…”郑氏的嗓音平稳,但听得出来语气冷硬。
锦衣卫,慎刑司都是薛侯爷的人,且连皇帝都管不着,至今还捏在太上皇的手里。
国公爷若是进了这两个地方,只怕凶多吉少,要吃上一番苦头了。
两名暗卫刚出去,国公爷身边的侍卫段安,便举着火把回来了,到了郑氏跟前,急声禀报道:“夫人,国公爷在锦衣卫。”
郑氏的脸色这才有了变化,嗓音大了一些,“他锦衣卫抓人,也得需要个由头,国公爷到底犯了哪一桩罪了?”
段安跪下请罪,“属下无能。”
郑氏心知肚明,“能带走国公爷的人,你也拦不住。”
段安详细禀报道:“主子到大理寺的半路上,便被太上皇身边的王公公拦下,说昨日抓到了六年前鹰山之战的一位叛将,亲口指证秦家当年叛国,国公爷也有参与,谋害了先太子。”
‘呸——’郑氏气笑了,平日里一派端庄,此时也忍不住爆了粗口,“贼喊捉贼,还倒打一把,先太子乃我韩家的人,我韩家是有多愚蠢,自己杀自己人…人老了脸都不要了。”
可如今她能如何。
三个儿子,两个在人家手上,世子出了城还不知道是不是凶多吉少,郑氏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府上的人分成了三队,一队去城外保护世子的安危,另一队去敲宫门找昭德皇后,余下一队守住国公府。
韩千君立在郑氏身旁,一只手都要被二嫂捏碎了,手脚也逐渐凉了起来,突然道:“我去。”
“我去见姑母。”韩千君对郑氏道:“母亲速速派人,沿路去敲父亲部曲的府门,今夜务必要确保府邸的安全。”别像当年的秦家一般,等众人回过神,人已经没了。
韩千君见过秦家的惨状,没等郑氏回复,转身就走,急声吩咐鸣春,“备马车。”
她知道秦家的案子不会那么容易,但没料到有皇帝和昭德皇后的庇佑,国公爷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心突突的跳着,夜风从斗篷底下灌进来,手脚冷得发麻,火把冒着浓烟穿梭在夜色中,彷佛又回到了六年前。
这节骨眼上到处都差人手,且她熟门熟路,进宫去找昭德皇后最适合不过,郑氏派了两个武婢跟着,叮嘱道:“不可硬碰硬,情况不对,立马回来…”
正是半夜,外面一团漆黑,除了她一辆马车路上几乎无人,很安宁,但这份安宁并不属于国公府。
韩千君走的是南宫门,这条路她熟悉,守门的人认得她的脸,不会拦着她。
马车到了宫门口,韩千君裹了裹身上的斗篷,把自己一张脸露出来,对守门的侍卫道:“国公府三娘子韩千君,接陛下口谕面圣。”
她若是说去见昭德皇后,一定会被拒绝,此时最管用的,便是她前贵妃娘娘的身份。
谁知对面的侍卫今夜却如同瞎了眼睛,并没让道,弓腰垂目道:“韩娘子请回吧,今夜谁也不能进宫。”
“我若偏要进呢?”韩千君脚步往前冲,让他开门,“你们连陛下的口谕都不听了?”
![[红楼]林氏第一神医](/img/68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