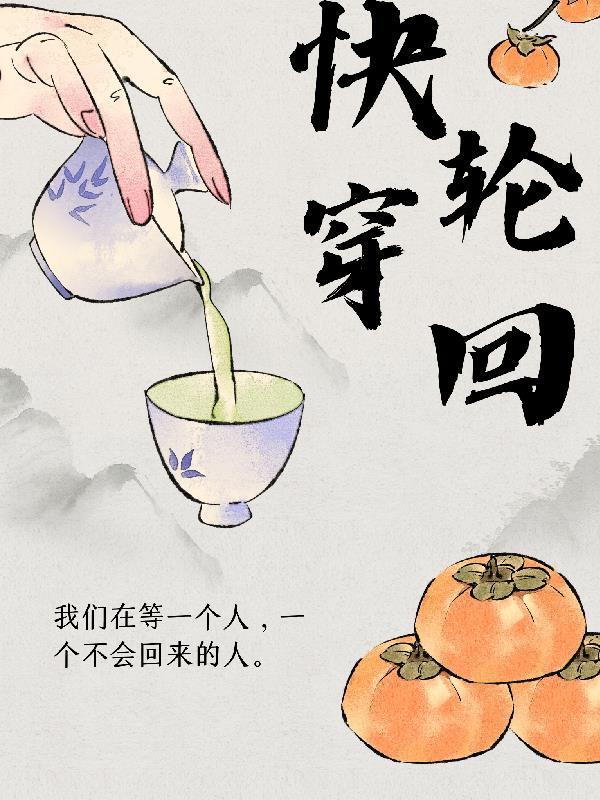腐书网>娇帐鹿时眠讲了什么 > 第100章 第 100 章 乱了方寸(第2页)
第100章 第 100 章 乱了方寸(第2页)
姜令檀陷在他怀里,脖颈上沁着细汗,闻言不可置信瞪圆了眼睛。
什麽狗屁选择,她都不愿意。
“考虑好了吗。”谢珩轻笑一声,十分怜惜揉了揉她的头发。
姜令檀鼓着绯红的唇瓣,用沉默表示拒绝和抗议。
谢珩从提出这个要求开始,他就没想过她会服软同意,但他也没打算就此放过她。
两人就这样耗着,才过完一刻钟不久,她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勉强挣扎想要用舌尖把玉蝉吐出来,然而他长指不轻不重抵在她唇上。
看这情形,她好像真的快濒临绝境了。
“跟孤回玉京?”谢珩淡声问。
姜令檀瞳孔颤了颤,用力抿紧了唇,不说话。
等三刻钟近尾声时,姜令檀整个人已经有些晕乎乎的,她费力挣扎着,口齿不清,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麽,嗓子里只剩若有若无细软的哭腔:“我不回去。”
“你会的。”他声音轻得如同情人的呢喃。
所有的反抗成了徒劳,像是被火烧着的身体里记忆颠倒混乱,她纤指死死攥着他的袖缘,红润的唇因为抿的时间过长已经充血红肿,就像涂了秾丽的口脂,再配上那双泪眼蒙眬失神的眼睛,美得叫人窒息。
姜令檀不知道自己怎麽睡着的,昏昏沉沉中有人给她喂了蜜水,又用湿热的帕子帮她仔仔细细擦净脸上的热汗,等一觉醒来,屋中只有朦胧的烛影。
“醒了。”灯影里,男人长身玉立,一双眼眸正静静看着她。
姜令檀看着太子,半晌回不过神。
此时正值深夜,她躺在书房的暖榻上,身上盖着他的大氅。
“我。”才说一个字,声音就哑得不成样子。
“先把药喝了。”谢珩端了碗还冒着热气的汤药递给她。
姜令檀眉心一蹙,身体忍不住瑟缩一下,她明明在生气,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从西靖回来後,他的举动让她觉得十分危险,那双眼睛太深太沉,逼迫她时,总透着叫她说不上来的冷意。
“听话。”谢珩看着她。
姜令檀没有再拒绝,她费力挣扎着坐起来,擡手接过药碗。
“你就算罚我,我也不回玉京。”她喝完药,看着他,态度少有地强势。
谢珩沉默一阵,只是眯着眼看她许久。
有时候他竟然觉得是自己小瞧了她,被逼到那样的程度,在晕过去之前,她依旧不愿回玉京。
“罢了。”
“那就帮孤写封秘信吧。”谢珩指了指书桌上已经摆好的空白信纸,还有蘸好墨汁的玉兔毫。
姜令檀呼吸顿了顿,眼中防范的情绪很明显。
谢珩重新斟了一杯热茶,端在手里也不喝,他往後退开些:“孤念出来,你写就是。”
姜令檀站起来,整个人踉跄一下,到底是咬牙一步一步走到书桌後方坐下。
她伸手执笔,慢慢擡头,对上他的视线。
他眉眼深邃似浓墨,情绪却极淡:“永安十年,柱国公府齐氏叛国通敌一案。”
“案情有变,兹事体大,理当重查。”
短短二十八个字,落进姜令檀耳中犹似雷鸣,把她心底那些微不足道的防范心,击得粉碎。
她指尖僵冷,差点握不住笔,就连墨汁溅落也毫无所觉。
谢珩静静看着,嘴角噙着一丝笑,终于端起茶盏慢慢饮了一口,昏黄灯芒下氤氲水汽飘散在空气中,如丝如缕,像是要把她给缠住。
“怎麽不写了?”
姜令檀掌心一抖,大团的乌墨在信纸上晕染开。
她被他盯得慌乱,语无伦次:“我这就写。”
到底是心境不平,连着写废几张纸,她都没能写出一张像样的字。
咬着唇,掌心掐着失力的手腕,暗暗吸了口气,正打算重新提笔。
这时谢珩已经搁下茶盏,走到她身後站定。
“永安十年,齐居正病故次日,父皇得了从西靖贺兰氏送到玉京的消息,那封密信谏言柱国公通敌叛国,证据确凿。”
“信中有一那张据说是齐居正的亲笔信,被烧毁了一半,还印了他的私章。”
“只是後来大理寺的探子翻遍柱国公府上下,几乎是挖地三尺,也没能寻出那枚印章。”
谢珩粗粝的手掌把她柔软的掌心几乎整个包进去,微微使力气,带动她颤抖不已的手腕,从容不迫在信纸上写下那二十八个字。
姜令檀不知道太子为何要告诉她这些,被那样滚烫的手握着。
她终究是无法镇定,乱了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