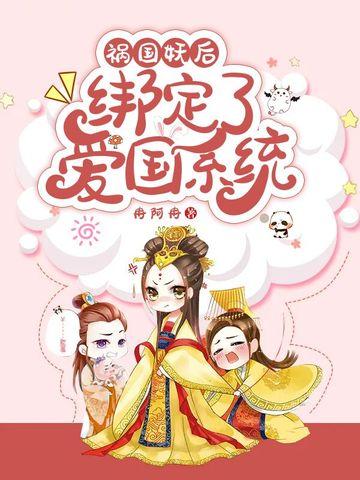腐书网>在雪融化之前by听灯全文免费阅读 > 第六十章 岔路(第2页)
第六十章 岔路(第2页)
梁冰想了想,还是问出口:“那你怎麽不见我”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此一时彼一时,即便见面,也不过是遥遥相望,形同陌路。
燕雪舟只停顿了一秒,凝着她的眼睛,“……我想再多给你一点时间。”
梁冰心神微颤,当时她的确元气大伤,别无他法,只有时间才能抚平。
等她忘记,等她恢复,等她自我疗愈。
可他本应是最该对她心存怨怼的人,到头来,竟然成为了最懂得她的人。
短暂的静默後,梁冰又听他问:“我等到了吗”
她思绪僵滞,不知该如何作答,正陷入两难之际,他蓦地轻笑了下,自问自答,“算是等到了吧。”
梁冰心不安理不得,却还是顺着台阶下来,问起他求学的事情,又说她上次去北京来去匆忙,还没好好玩儿过呢,下次再去她想爬长城,参观国家博物院,去雍和宫烧香祈福。
燕雪舟不屑,“净挑些没劲的地方。”
梁冰很认真的问:“那你说哪里好玩儿”
燕雪舟忽然沉默了一会儿,像是突发奇想,临时提议道:“下个周末,我带你去。”
反正学校里没什麽事,梁冰点头应承下来,“嗯。”
下午,梁冰把最近经手的文件和项目整理好归档,刚做完就接到了宋一鸣的电话,他语气有些奇怪,“你现在方便出来一趟吗”
“怎麽了”
“我好像给你惹麻烦了。”
等梁冰来到研发中心对面的肯德基,看到那个满面沧桑的中年女人时,才明白宋一鸣指的是什麽,不过不准确,麻烦不是他惹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
三年前,梁冰实名举报时在“一鸣惊人”的上出过镜,被她的生母岳秀玲看到,按照文後提供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找了过来,并声泪俱下地恳求宋一鸣,说如果他不管,她就直接去学校宿舍楼下堵人。
在梁冰的记忆里,她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连对方的轮廓和眉眼都是模糊而陌生的。她送走宋一鸣,到柜台前买了两杯可乐,用托盘端过来,推到岳秀玲面前一杯,“你找我有什麽事吗”
“我……我——”岳秀玲吞吞吐吐的,艰涩开口,“我想跟你借点钱。”
无旧可叙,只能开门见山。
梁冰握着可乐的手指像是冻僵了,她从骨子里觉得发寒。
当下的场面实在太过滑稽,梁冰竟然笑了下,“且不说我根本没有钱,你到底怎麽会想起来找我借钱的”
“小宁,你弟弟……就是我後来又生的那个孩子,他生病了,医药费是个无底洞,家里能借的钱都借遍了,现在亲戚们见到我们都绕道走。”岳秀玲抽了下鼻子,瞥了眼研发中心的方向,“你不是在里面上班吗手头上不可能一点儿钱都没有吧。”
“会还的,我给你打借条。”她毫无所觉地说着颠三倒四的话,“有多少借多少。等小宁治好了病,我们缓过来了,肯定会还给你的。”
梁冰不想说话,不想动,甚至不想冲她发火。
她只觉得无力,连叹气都觉得累。
仿佛是眼看着好不容易挣扎出了困顿自己的那一滩泥淖,却在最後一刻被人猛地拖了回去。
梁冰抿紧唇,完全没留任何馀地的拒绝她,“你找错人了,我没有钱,更没有义务负担你儿子的医药费。”
不待岳秀玲再说话,梁冰站起身,漠然道:“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你以後不要再来找我了。”
推开那两扇玻璃门前,梁冰听到身後传来近乎低吼的威胁,没什麽底气的样子,“你不管,你不管,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信了……”
梁冰出来的急,只穿了件薄外套,冷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从肌理吹进骨头缝,又从血液漫进心脏,也把剩下的那些话吞没。
还没走进研发中心的大楼,手机铃声就不屈不挠地响了起来,梁冰机械地接通,贴在耳边,“喂”
“是我。”李慧英漠声通知她,“今年是恪儿五周年,前些日子我梦到他了,他跟我说嫌庙里太吵,我就买了块墓地,打算让他入土为安。到时候会有个祭奠仪式,你……回来吗”
梁冰张了张嘴,感觉喉咙像是被东西锈住了,她很努力地,好半天才发出声音,在风里显得有些空洞,“……什麽时候”
“我找人查的黄历,下个周末。”说完,又没好气地冷下声音来,“没空就算了,也不差你一个。”
“知道了。”
梁冰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