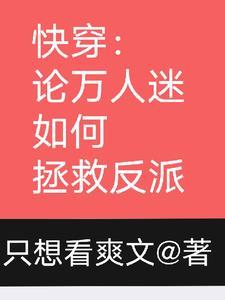腐书网>末世娇花np > 第54章 采花贼(第2页)
第54章 采花贼(第2页)
虞岱一边生气自己把人弄丢了,一边又对尤眠总想从他身边离开却完全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而感到无可奈何。
明明就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却偏生又总藏着一丝戒备。
谁也不能越过他心里那道防线,一旦察觉到有失控的风险,他就宁可不要也不敢接受。
虞岱掌心下是肌理细腻的脖子,他虚虚握住在手中揉捏把玩:“你和万岁山呢?他有没有碰你,嗯?”
尤眠抽抽搭搭的:“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不认识?”虞岱冷笑一声,低头咬他的脖颈,手指隔着衣服揉弄,“那白天和你站在一起的男人是谁?你还让他牵你的手。”
“那是我叔叔,不是你说的什麽万岁山”,尤眠闷哼一声,嘴唇颤抖着扭头看向虞岱,眼中有求饶的意思,眼尾因为剧烈的快感红的像是精心调制的胭脂。
虞岱盯着他的眼睛,居高临下睨着他:“都叫上叔叔了,是吗?宝贝儿,你确定要这样惹我生气?”
尤眠让他说呆了,坐在他腿上一动不动,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汇聚在下巴上凝成一滴一滴。
虞岱的眼神幽深得像是寒潭里的水:“不仅不记得我了,现在还因为别的男人掉眼泪,真是欠收拾了。”
言罢,便不再给尤眠任何解释和缓冲的机会。
手臂突然被扣住,虞岱拉着他往後一扯,身体重重被摁了下去,尤眠尖叫一声,两只手又飞速捂紧了自己的嘴巴,整个人都在细细发着抖。
“不要……”
“听不见。”
虞岱眉眼漆黑,死死扣住他的腰身,尤眠宛如在一艘汹涌波澜的大海上航行,一下被巨大风浪掀翻,一下又被救命绳索拽住扯回来。
“说。”
尤眠声音破碎:“说…说什麽?”
“说你永远爱我,永远不会再离开我。”
尤眠忽然觉得胸口很烫,胸腔好像被千斤重的东西挤压着,无法呼吸,他开始大口喘气,虞岱吻他,像要剥夺,又像是要帮助他呼吸。
却仍是不肯放过他,要尤眠一个字一个字的重复他说的话,又看见桌子上有纸和笔,便毫不费力抱着尤眠将他压在了冰冷的桌子上。
虞岱从後面揉他,进入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深度,尤眠傻乎乎的掉眼泪,一双眸子像是被揉皱的湖水,脖颈被咬的要滴血,又疼又麻。
“疼了才会长记性”,虞岱丝毫不因为这些眼泪而怜香惜玉,尤眠的胸前磨在桌子上,纸张被洇湿,颤颤巍巍的写着在他看来莫名其妙的保证书。
最後歪歪扭扭签上名字之後虞岱总算满意了些,将纸张叠起收好,又拽着尤眠陷入欲望的漩涡。
虞岱眼中藏着狂风暴雨,黑压压一片,却终是慢慢归于一片不见底的平静。
昏过去又被弄醒,如此反复,直到凌晨才落入温暖的怀抱,虞岱把头轻轻埋入他布满痕迹的胸膛,抱紧他。
以往都是尤眠贴着他,现在发生了颠倒,像怀里藏了一只没有安全感的大型狼犬。
他想要虞岱好,没成想虞岱却心甘情愿低了头。
他留下那样一张折辱人的字条,虞岱却还是找来了,酸涩的情绪在胸口纠缠,尤眠希望着,虞岱不要找他,又期望着,虞岱不能不要他。
尤眠有些失神,嘴唇红肿可怜的喃喃:“你这个采花贼可真是胆大包天,这麽没有防备心,也不怕我一刀扎破你的心脏。”
再有一会儿,尤眠就要起床进行每日必须的祷告了,尽管身体很累,现下也睡不着,他极少有这样事後清醒的时候,也极少像这样,单手支着腮,安静看他。
男人眼下有青色的黑眼圈,看样子为了找他,也是废了很大的一番功夫。
他的手不自觉摸了上去。
尤眠总被人夸长的好看。
但实际上,他觉得虞岱长得更好,棱角分明,眉目冷峻,高挺的鼻梁随着他指尖的动作,微微拧着,又在熟悉的气息中很快舒展。
不那麽像现在这般放松的时候,虞岱总是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冷漠气场,叫人不敢轻易和他对视,也轻易发现不了他的好看。
“睡吧”,尤眠合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