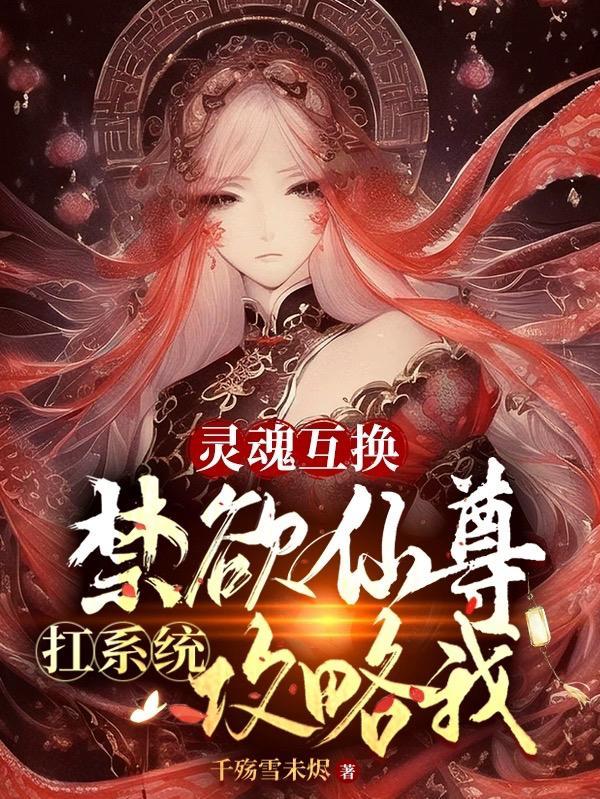腐书网>剧情都崩了还快什么穿在线阅读 > 第三百八十四章 张天娇被抓(第1页)
第三百八十四章 张天娇被抓(第1页)
龙傲傲义点点头:“没错,你一看就是一副肾虚阳痿的模样。要不是张喜华,她绝对得不到你。光靠你自己努力,那得等到你努力到老死,都得不到张喜华。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两个人成全。
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不要自卑,你想要相信,老天爷让你经历这种事,一定是有原因。说不定是因为你真的很贱,贱到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这一点我很认可你。不过也是辛苦你了,自身处境都这么艰难了。真的很痛苦。”
王罗:“……”谢谢,并不需要你的认可。我不难过。
龙傲傲给王罗妻子煽风点火:“你要真想回收垃圾。我有一个绝佳的办法,一劳永逸。如何杜绝老公经常性出轨了,如何让老公和你恩爱如姐妹,用了这个办法,你的烦恼不再是烦恼。”
王罗妻子:“什么办法。”
龙傲傲用手做了一个切了的手势说:“太监他……怎么样,有没有很心动。当不成夫妻,以后当姐妹也不错。姐妹一生一起走,没有男人也没有狗。再打断他的狗腿,姐妹情深似金花,没事就当悲伤蛙。”
王罗:“!!!”
王罗妻子:“……”
小七:你为了押韵,真的什么话都说的出来啊。
龙傲傲看着王罗妻子脸上的犹豫,深沉的说:“我知道你还有犹豫。没有关系,让你去压死他们,对你太不友好了。对你的体重也不友好,这简直就是侮辱你的脂肪……”说着他转身就走。
过了一会儿,龙傲傲扛着一根扁担冲了过来。他郑重的把扁担交到王罗妻子手上:“用这个打,我支持你。这是在我能力范围内,能给你的最好的帮助了。加油,小蛙。”
王罗妻子愣愣的说:“小蛙是谁?”
龙傲傲看着她微笑:“小傻瓜,你啊。你现在瞪大眼睛都样子,特别像一只悲伤蛙。哦,对了,你不需要知道悲伤蛙是谁?你只要知道你很像就好了。”
王罗妻子:“……”
王罗妻子拿着扁担最终也没有打下去。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在他打下去之前,警察来了。
警察们走过来的时候,花沟村的村民们都很震惊。所有人心里想的都是,在外面养小老婆居然会被抓么。
直到警察把张天骄和王罗给控制了起来。他们才明白怎么回事。
警察看着王罗严肃的说:“王罗,你奸**女的行为已经证据确凿了。跟我回去吧。还有张天骄,你是帮凶。你帮助王罗犯罪,也要跟我们回去。”
张母一听,张天骄居然还掺和了这些事。身子一软,跌倒在地上:“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儿子他怎么会干这种事。”
警察:“证据确凿。”
张母喃喃的说话:“……”
张天骄拼命挣扎:“不关我的事。是王罗逼我做的,他让我去给他找年轻好看的女孩子来给他玩。不然就杀了我全家。我也是没有办法。”
王罗激动的对张天骄吐了口水:“我呸,你放屁。明明就是你主动跟我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玩到年轻漂亮的女人。你说让我外面宣布招年轻女工的启示,专门面向那种从农村上来打工的女的。
等他们过来面试,好看的就给他们下点药,直接上了。最后给点钱打发了就可以了。我都是听了你的怂恿。”
这一波狗咬狗,令在场的人大开眼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之二人。
张天骄听着围观村民对他的议论,恨不得把头埋到地上。
龙傲傲走到警察旁边商量到:“警察同志,你看我们棍子都准备好。正打算为祖国好好的鞭笞这两个不要脸的混蛋。能打完这一波在走吧。”
警察无语的对龙傲傲说:“……动用私刑也是犯法的。”
龙傲傲自言自语:“切,白准备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看王罗嚎叫。没看到,感觉损失了一个亿。周老狗做事一点也不靠谱,害我损失了一个亿。他得赔我两个亿才行。”
周书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龙傲傲旁边,好笑的问:“你怎么知道是我?”
龙傲傲翻了个白眼:“老子掐指一算,就知道你个狗批没安好心。你一肚子全是坏水,亏我爹还以为是我染指了你。殊不知,你那心肠就没白过。”
周书墨:“……”他无奈的笑笑:“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张天骄的消息。也知道他和王罗混在了一起。本来我就让人在调查王罗。没想到张喜华突然带着王罗回了花沟村,那岂不是撞枪口上了么。
她那老婆,是我让人去通知的。王罗是入赘的。这些年,一直都是他老婆当家。知道老公在外面养狐狸精,气冲冲的就冲过来的。
于是,我就顺着这个机会,让人把调查结果拿去报了警。才有了现在这个对方会谈的结果。”
龙傲傲:“呸,就你聪明,就你牛逼。这么能装逼,你砸不去当老黄牛呢,它那重点部位,还差一个呀。”
周书墨:“……”
而在这场闹剧中,只剩下张喜华一个人接受众人的谴责。
张母红着眼眶走到张喜华旁边:“喜华,你告诉我。你只不知道你弟在外面干的那些腌臜的事。”
张喜华猛烈的摇头:“我不知道,妈,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弟弟他只是王罗的助手。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平时干什么”
龙傲傲:“诶,妈,你别问她了,好得考虑一下她的智商吧。她最多当个小三就已经用光了她的脑细胞了,不然她早就上位当正宫。那还有多余的脑细胞贡献给张天骄他们。”
面对张喜华躲闪的眼神,张母恨铁不成钢的说:“我和你爸,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的么。你这是作风有问题。是不是张家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报应到你们身上了。怎么你们一个个成了这样子。”
张父也跟突然老了十几岁一样,低头抽着烟,沉默不语。那烟甚至已经烧到手,他都毫无知觉。